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1998年开始,毕淑敏攻读北师大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她开了诊所,直面一线的心理咨询者,并通过一系列心理学案例的“非虚构”写作和演讲,治病救人。
在我眼里,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悲天悯人的医生,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作为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以笔为旗,身体力行,用文学和医学的叠加,在暗夜中,用爱与希望点亮生命之灯。
我喜欢她的作品。1995年夏天,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毕淑敏,当时的访谈叫《生命,永远的追问》。时隔二十四年,2019年12月5日,我在北京再次采访毕淑敏,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话题涉及科技未来、心理学、教育,最后回到文学。
毕淑敏家的客厅,挂着一幅巨大油画,取材于西藏阿里的山川地貌,油画左下角,有一个红十字帐篷和一匹白马,描绘她当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卫生员的经历。这是一个喜欢毕淑敏作品的画家,依照从她文学作品中得来的印象,倾心创作出来的,然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她。我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
——张英

毕淑敏, 1952年生于新疆。1969年入伍,曾在西藏阿里工作十一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先后获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曾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红处方》 《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及《当代》《昆仑》《小说月报》《北京文学》等刊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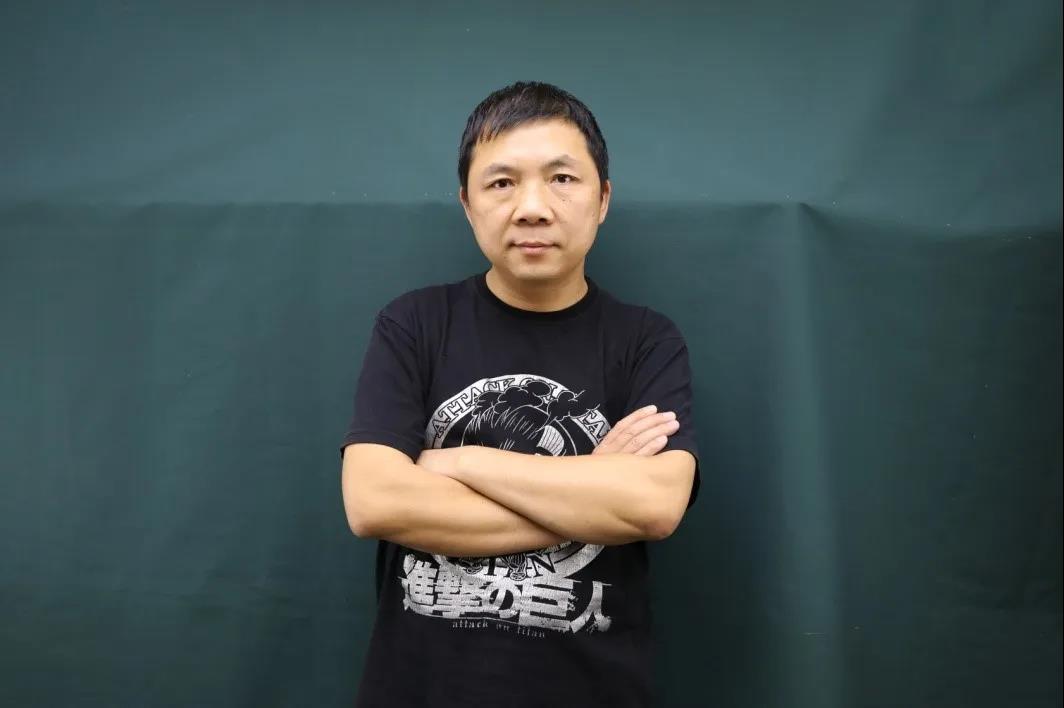
张英,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著有《中国文化现场》。现供职腾讯网,《腾云》杂志执行副主编,腾讯华文好书奖、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奖创办人。
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张英:医生的工作对你的作家生涯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毕淑敏:医学对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唤起了我对生命的的珍视。我从事医学二十多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我影响甚大。有人常常说起鲁迅的弃医从文,但鲁迅并没有真正当过医生,他医学专业还没毕业就离开了,没有进入临床工作。郭沫若刚开始也是学医,进入临床实习后,因他小时候得过热病,听力受损,戴上听诊器却听不到病人的心音,只能放弃从医。
我在西藏时,并没有想到今后要写作,而是一门心思埋头学习医学知识。多年的医学训练,让我无法放弃一个医生的眼光。我写作的时候,很崇尚真实。医学这个职业,涉及人的生命,医生必须务实。你很难看到一个表情行为特别乖张的医生。医学训练让我严谨冷静,注重精确性。
其次,我深刻尊崇众生平等。无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外在,他的身体一旦被打开,内部的器官在解剖学上高度相似。众生平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对我的内心留下了非常强烈的烙印。有读者朋友对我说,从我的小说里,能看到一种浓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觉得这要归结于我受过的医学训练。年头长了,浸染引发出来。
我后来学习了心理学相关知识,认识到人的身心一体。人不是一个纯粹装着各个器官的皮肤容器。人的心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一部分,就像脑科学一样,其实都有准确的定位,蕴含着我们很难破解的部分。人的身心应和谐统一。
这些提高了我的观察力。中医说“望而知之谓之神”,“神”我们做不到,但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西医虽没有这个说法,但也号召医生要仔细观察。观察不仅仅限于他的表面现象,还要去探索他的内在。
心理医生的训练,让你能见微知著。从一个人的一个小动作,或是一个表情,或者他的口头语,有可能分析出深层的东西。
张英:十六岁当兵,怎么就去了西藏?
毕淑敏:1969年,我应征入伍,特别想当一个通信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先坐火车,然后是十二天汽车,一路跋涉,千辛万苦,抵达西藏阿里军分区。它的前身是阿里骑兵支队,我们五个女战士,是那里的第一批女兵。
十六岁离开北京,来到西藏,对于花季少女的我来说,直接掉入了冰雪季。一路上,雪山连绵不断,高原空气稀薄,满目荒芜。人缺氧时会喘不过气,如同老太婆。可以说,从灵魂到身体,都受到极大震动。
那时的我无法想象,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如此遥远、如此悲壮并且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阿里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千五百米,氧分压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在那里,活下去是每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一次军事训练,风雪之夜,部队要穿越无人区,翻越六千米的高山。寒风刺骨、极度缺氧,所有的身体感官都在经受痛苦。肺压得像纸片一样,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吸进足够的氧气,大脑因为缺氧,不断呈现空白甚至出现幻觉。
我身背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加上背包,负重将近七十斤。泰山般压在身上,举步维艰。从半夜出发到目的地,总计六十公里。无法忍受时,我第一次想到了用死亡结束这地狱般的行程。
到下午四点,才走了一半路程。我决定自杀。再也走不动一步,肺里吸不到一点氧气,只觉得自己要吐血。高原的夜晚来得非常早,当时我决定不再活着了,找个悬崖,纵身而下。这样,一是自己解脱了,二是别人分辨不出我是自杀,就能得到“烈士”名声。对我个人没什么用了,但家里人知道我的死讯后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最后,我还是没有跳下去。因为身旁就是战友,我若滚下去,也许会拖累别人,人家并不愿意死啊。我在极度寒冷中,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到达宿营地。这种极端体验,让我突然间对生命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英:你在西藏阿里当兵的时候,是属于全科医生吗?
毕淑敏:在阿里时候,还没有“全科医生”这个概念。因为距离上级野战医院有一千二百公里之遥,我们必须掌握诊疗各种疾病的本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全科医生”了。当地牧民,称我们为“金珠玛米”的曼巴。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砸碎锁链的兵的医生”。
那时,边疆条件较差,无法细分那么多科目,不管什么样的病,来了你都得看,治病救人,手起刀落。你要是把患者转院,颠簸一千二百公里,那人很可能就死了。环境形势所迫,你“内外妇儿”都要去救。转业回到北京以后,我就专心做内科医生了。
在西藏当兵,距离死亡非常之近。面对年轻战友的生命突然消失,会受到强烈震撼。战友牺牲,尸体无法火化,都是就地土葬。山高路远,万里迢迢,他们的亲人也无法赶来追思。我们这些女卫生员,为他们整理遗容,擦拭尸身,成为他们最后的送行人和祭奠者。
一名边防战士急需输血。一个连的适宜血型都几乎抽光了,连长着急说,再这样抽下去,如果有了战斗任务,我连的战斗力会受损。后来一查血型,我的血型和那个战士相符,我们班的女战士就抽血给他,我也在其中。最终救活了这名战士。我当时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我曾经对家里人说,如果我去世,火化的时候,给我穿上旧的丝绸衣服吧。它很容易燃烧,又比较舒服。这个念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存在于心。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厢情愿地以为死亡遥远,是他人的事。感谢藏北经历,让我在年纪轻轻时,就知道死亡必不可免,生命万分脆弱。
可能因为我做过医生,在这个问题上,我清楚地认识到: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遭逢的事。人从出生开始,就向着生命的终点挺进。既然死亡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地,就不应该回避它。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没有抵达终点之前,要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丰富,尽力使人生少遗憾,多一些幸福和完美。然后,顺其自然,平静抵达终点。
张英:你早期的《雪山女兵》等小说里头,写的都是战友的真人真事,让人震撼,和平年代里的人是没法想象的。
毕淑敏:西藏阿里是未定边界。你在地图上会看到那个标识,指的是和印度的未定国界。作为中国军人,你必须站在那儿执勤,必须守住阵地,不然边界上很可能出现摩擦,甚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战友牺牲后,给卫生科送来遗体换尸衣。我见过一个士兵的腹部中弹,腰腹贯通伤。肠子流了出来,战友就把一个饭碗扣在他的肚子上,想给他的肠子保暖。于是饭碗和一堆流出的肠子冻成一个血色冰坨。
没法换尸衣。军服没有那么肥大,肚子上鼓出一大堆,扣不上扣子。有人建议把碗拿下来,用酒精喷灯解冻。我实在不忍心让已经牺牲的烈士受苦,决定把这个碗一起下葬。找来最大号的新军装,从背后把衣服剪开,总算给他穿上衣服。从正面看,还挺威武的。
当时的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领导,现在都快九十岁了。如今战友聚会时,他对我说,你当时是班长,我给你派了任务,让你们十几岁的女娃娃给赤身裸体的牺牲战士擦洗、换衣服、清理浑身血迹……对不起你们啊……我跟他讲:您千万别这么说。牺牲战友就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亲人不能送他,我们就是他的妹妹们,这都是战友应该做的事儿。这些经历,对我的三观有很大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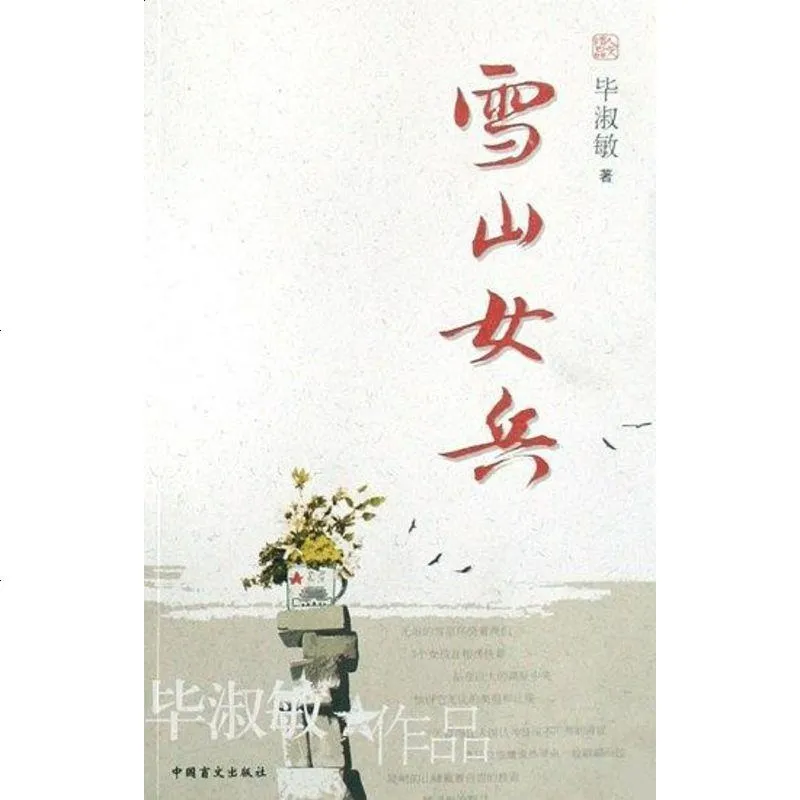
毕淑敏作品《雪山女兵》
张英: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被彻底改变了。
毕淑敏: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我一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人生最宝贵的日子,都是和人的生与死有关。加上当医生的经历,自然会让我的作品对于人的生命倾注热情和关切。生命,光有长度是不完整的,还得有质量。你活的心境凄惨,生命的存在变成完全在感受痛苦,是不正常的。事在人为,可以调整改变。我学习心理学之后,发现人是可以改变的,人能够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
那时几乎无书可读。唯一的图书是部队发的《鲁迅全集》。完整的一套书,每天工作忙完,就在夜里看书,认真地把《鲁迅全集》看了几遍。
鲁迅说他的的确确是常常在解剖他人,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我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从解剖自己下笔。
在阿里高原时,有一天,我们用担架抬着患肝癌病故的牧羊人,爬上人迹绝踪的山顶,实施“天葬”。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的秃鹫,粉碎的身体器官,想起牧羊人生前的笑容……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生。我在营地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被偶尔上山的军报记者抄去,发表在报纸上。
现在西藏当兵,不会让内地人在那里工作那么久了。我在的那个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尚没有轮换机制,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几年换一次。
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
张英:你转业回北京后,开始文学创作。王蒙评价你说:“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毕淑敏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太听话了。”
毕淑敏:我回北京后,转业在北京铜厂当卫生所所长。1986年,当时我三十四岁,试着写了处女作《昆仑殇》。完稿后,是我爱人骑车把小说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时军队有本杂志是双月刊,叫《昆仑》。他们在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看了稿子,发在了1987年的《昆仑》第四期头题。
当时对我来说,初试写作,作品投稿到哪儿,最终能不能发表,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把它写完了,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写完后,是我先生骑着车,把文稿送到了解放军文艺社。因为他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小说中,保尔·柯察金写了一篇稿子,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为此差点自杀。他说,还是自己送去比较保险。
在那之前,我没写过短篇,没在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作品,连篇散文都没有。当时编辑部看这个小说以后,都在说这个小说是不是哪个男作家化名写出来的。后来又觉得写的是西藏边防部队,没有那儿的生活经历也写不出来,作者的名字又是个女的,有点奇怪。
他们约我到杂志社编辑部谈稿子,提了个要求,让我和我先生一块儿去。我当时不明白是何用意,后来发觉他们想看看是否我丈夫代笔。交谈中,特别是涉及小说中的细节,我先生完全不知道,都是我来回答,他们方才确认这个稿子是我写的。
写了两个中篇小说后,1988年,我就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同学中有迟子建、严歌苓、刘震云、莫言、余华等。上学后,我觉得也可以试着写写城市生活、医学题材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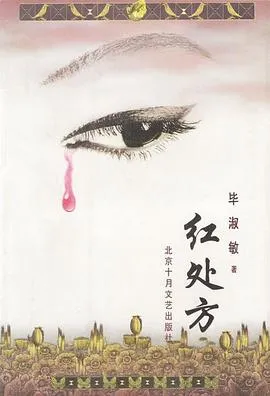
张英:王蒙还评价说:“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家,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我觉得王蒙的话很对。像《红处方》这个作品,你是抱着怎样的责任感去写的?
毕淑敏:没有人安排,是自己主动写的。《红处方》那个年代,社会上吸毒现象萌生。我作为一个医生出身的作家,对此不理解,有危机感。
别的天灾人祸,比如得癌症、心血管疾病,有些客观的遗传因素,某种程度的身不由己。可是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能主动去吸毒,做故意残害生命的事情呢?我到戒毒医院实地深入生活,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人在觉得幸福的时候,大脑皮层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内啡肽,而吗啡的化学性质,恰好模仿了人在幸福时候的那种物质。我很想用自己的笔,说清楚这件事情。毒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诱惑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去尝试它?因为开始的时候,它不让你觉得那么可怕,会让你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那是很飘浮很放松的感觉。你一旦上瘾,就难以逃脱它邪恶的魔爪。
写《红处方》的动机,来自对生命的责任感。想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学作品,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故事主人公简方宁选择自杀去殉圣洁的事业,以此昭示人类的信念有远超于毒品之上的力量。
张英:后来,《红处方》的社会反响很大,又拍了电视剧,你为什么没有写剧本?
毕淑敏:在《红处方》里,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人性中有许多黑洞,生活中隐藏着太多陷阱,我想用一个作家的良知去提醒人们的注意。
《红处方》的电视剧我看了。小说和剧本,还是有很大差异。我尊重改编者。直到现在,我没写过电视剧本。术业有专攻,我对剧本写作没有专门研究,很可能做不好。
张英:《血玲珑》特别像一个非虚构的新闻,那个小说是怎么来的?
毕淑敏:这个小说,最早来源于我当医生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病例。孩子死了,我想到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是否可以做骨髓移植。当时的中国医学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
《血玲珑》电视剧播出后,有一个电视台跟我说,现在真的有这种疗法了,你愿不愿意和这样的家长见个面聊聊?一定是个很感人的节目。我说,祝福那个家庭幸福。我写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小说。谢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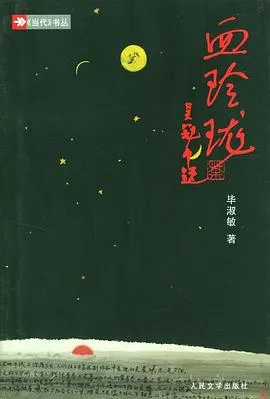
毕淑敏作品《血玲珑》
“非典”病毒和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