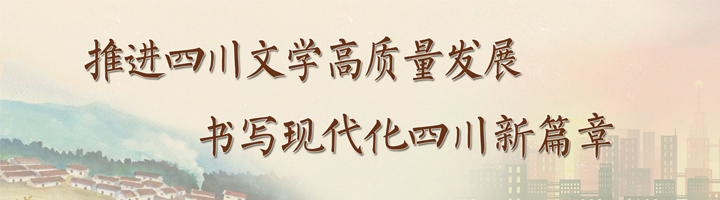2015年12月10日,兰池村村支书王崇华从田坝镇领回一个上面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崇华至今回想起来仍是记忆犹新。那时,当会上一宣布,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娃来到自己面前,王崇华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遭了,咋给兰池村整个娃来呢?唉,这下咋整,完了完了……原本兴冲冲来的,回去时闷闷地,生生没有了语言。
几年后回忆起来,王崇华意味深长地咂着嘴说,他看走眼了,他小看这些年轻人了。现在的年轻人,确切地说,是组织上派来的这些年轻人,是真的来帮咱们的。
上篇 杨川的故事
甘洛,给了杨川很多经历,痛苦、喜悦、感动、纠结,还有流下了自记事以来第一次委屈的眼泪。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微薄的力量能起的作用有多大……
王崇华说的这个娃就是杨川。杨川是四川省地矿局所属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训练部基础教育系的一名老师。那年,省地矿局一次选派了11名优秀干部到凉山州甘洛县田坝镇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开展精准扶贫。
杨川是这11名干部之一。那年他26岁,正是春风得意、壮志未酬的年岁。学院公布选派第一书记告示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报了名。当然,他也征求了正在热恋中的女朋友的意见。
“她是支持的。”在后来的采访中,杨川很认真地对我说,但声音很小。杨川虽然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很秀气。他说,女朋友其实是很善解人意的。看得出来,对他来说,对后来和女朋友的分手,这个中滋味是很难道得清楚的。
其实,学院一开始定的并不是杨川。学院的教职员工报名很积极,院党委研究后确定了一名要求强烈的年轻女老师,女老师还兴冲冲地去省上参加了统一培训。待培训结束临开拔,学院被通知另派人。原因估计是各单位选派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一个女的去了总有很多不便。
那天,杨川正带着一群学生在球场上上课,教务处主任来告诉了他这个通知。杨川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发了。
在和其他第一书记汇合后,杨川遭到了同仁们善意的挤兑,“本来还盼着有个帼国英雄来增加点亮色,你倒好,不仅让我们美好的愿望成泡影,还偏偏长这么帅……”
杨川的确是一表人才,单是一米八三的个儿就让人羡慕,由于大学学的又是体育,喜好运动,看上去伟岸挺拔,给原本那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增了几分彩。据说,这些优势,给他后来的工作开展带来了其他同事没有的便利。
对来甘洛扶贫,杨川其实没有多少心理准备,他没到过农村,因此想着多一种体验总是好的。来的那天,一路上他都感觉很新奇,尤其两边的大山这么大,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到了甘洛又下了雪,他很是有几分兴奋。
但很快他就愁上了,因为错过了培训,什么任务呀、政策呀、方法呀等等,一切都很茫然,他必须得加紧补课。
甘洛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县有7个镇、21个乡,人口以彝族为主。1956年12月建县时,甘洛县名为呷洛县,因“呷”字读音与原地名误差太大,1959年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甘洛县。
从地理上看,甘洛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全为山地,岭高谷深,河谷地带间有台地斜坝与河边小坝,西部有较大的高山间狭长斜坝。县境东部是连绵数十里的特克哄哄山,由8座4000多米和60多座30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中部是马鞍山,为全县最高点,海拔4288米;南部高山重叠与凉山中部大山相接,额颇阿莫山高3905米;西部横亘着3922米的碧鸡山以及大药山、小药山、轿顶山等山。
来自越西的尼日河,从甘洛县西南入境,斜切全境,在境内又接纳斯觉河、甘洛河、田坝河等水流,于东北境注入大渡河。在那里,随便找一处山坡望去,巍峨的群山将一团团的山村环绕,尤其在早晨,被一层薄薄的雾遮着,很是美丽,像极了童话中的景。有诗人说,甘洛其实很小,一朵白云就可以将这座城市覆盖;甘洛也很大,她包容了人生的悲与喜。但在我看来,这种包容,更多的缘于这山的美丽和美丽的山对村落的环绕中,她不经意成为了一种包裹,以致这美丽的乡村中还有这么多的贫穷。
杨川要去的兰池村位于田坝镇西南方向,距离镇政府5公里,从田坝镇顺着田坝河向西过了县城边再前行3公里拐进一条陡坡泥路,就进了兰池村的地界。而要到村口,还得在坑坑洼洼的一条村道爬行约2公里。爬行当然不是手着地,只是坡有些陡,背自然就要躬着,形似爬了。
那时,杨川在村里还没有住处,每天要从镇上步行到村里,一般要走一个多小时。有时遇到村支书开着车,也就顺带捎个脚。
来甘洛的第二天,杨川就开始了每天早上7、8点钟从镇上出发赶到村里走村串户的日子,每天中午就简单吃点干粮,晚上9、10点钟再回到镇上。
此前一头雾水的他,通过恶补政策、找同事咨询讨教,对工作的开展渐渐有了些眉目。听同事说培训的时候,老师讲驻村工作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每天同老百姓唠唠磕、喝喝酒、唱唱歌,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能做到走村入户时狗不咬、猫不闹,到中午饭点时出去走一走,有老百姓叫你吃饭,那证明你已经融入村子,你的工作就已经步入正轨了。杨川听了忍不住想笑,有这么简单还叫攻坚吗?
兰池村平均海拔1500米。全村有4个小组265户,总人口1066人,其中彝族310人、藏族2人、汉族754人,贫困建档立卡户67户271人。全村有党员17人(正式党员17人、入党积极份子2人)。全村共有土地9200余亩,其中林地6000亩、耕地3200亩。
这些,就是杨川最初接收到的信息。而接下来,他得尽快和村民熟悉,才能开展工作。于是,在老村长的带领下,他开始一户一户地了解摸排情况。听人讲,“兰池”起源,是因为当地人擅长种植一种叫蓼蓝(兰子)的植物,以原始的工艺加工成生态植物染料蓝靛,然后出售给田坝的各大染坊,用于彝族人常穿的查尔瓦、粘嘎染色。但如今,这种工艺已被时代淘汰,只留下一个个蓝靛发酵池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兰池村的4个组分布在4个山头,像手掌伸出去的几个指头一样,主干路线在山脚,因此,每去一个山头都要从一个山头下到主干路线上,然后再去另一个山头。你看着不远,但当用计时器徒步一走才发现,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因此,一天下来走不到几户村民。好在人年轻、热情高,杨川不觉得累,只是彝族村民的名字很难记,一开始,走过不久就想不起来了,后来他就立马记在本上,可以不断回忆。随着走访的深入,那些枯燥的数字慢慢被具体的景象替代,村子的情况在杨川头脑里清晰起来……
全村找不到好房子,基本上都是破旧的土坯房,房内空空荡荡没几样家具,衣物床被也都是零乱地堆在床上。在这里,似乎家家户户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无所担忧。但村里人还是有怕的,最怕下暴雨。因为有不少人家的房子已出现裂缝,房基出现了滑坡征兆,这时经暴雨一冲,可能就全垮了。而村道基本都是泥巴路,坑坑洼洼,一下雨,汽车根本走不了,平时家家户户都靠骡子、马运送物资。而最难的就是读书的娃娃了,下雨时穿着雨鞋,经常一脚踩下去就拔不出来,只好光着脚走,深一脚、浅一脚,带着满腿的泥泞走到教室去读书。
全村可用耕地少,没有什么产业,有限的土地里种了些玉米、土豆、蔬菜,也基本是自用,还有些核桃自由生长,完全是靠天吃饭。所以,村民的收入多靠家里的劳力在外打工,而没有年轻劳动力的、家里有病人的就非常贫困了,一年下来,全村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
那些日子,杨川就在村民家里串,慢慢地,和村民熟悉了。每每进到家里,不论怎么贫穷,村民一般都会想法拿出酒来招待他。也从那个时候起,兰池村的村民记住了四川省地矿局这个名字,记住了省地矿局来了一群人在田坝镇。他们用心用情,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
一开始,杨川还不适应,虽然他还是有酒量的,但不习惯这样把酒当茶喝,更不理解这么贫困还要喝。但他知道,你不喝就会被主人认为是看不起他,说什么都白搭,所以也只有横下心来不讲究了。
村民喝酒有讲究的,也有不讲究的。条件好的把酒倒在碗里,条件差的就对着瓶子喝。杨川第一次对着瓶子喝心里是有障碍的,但他知道不喝是开展不好工作的,你不喝人家会一直看着你,看你有没有诚意,而且你若喝得比主人还多,他会觉得你厉害,敬重你,还会给你竖个大姆指,说:“你是这个!那就是兄弟了。”这种民风后来我在采访时也时常遇到,那次在木乃布日家采访,主人就热情拿出一瓶精装的酒说:“来!开瓶酒喝着耍哈。”我一听就乐了,妈呀!哪有没事喝酒玩的。我连忙一边摆手一边说谢谢。主人听我说有高血压倒也不勉强了(这也是扶贫工作队潜移默化工作的结果),但说,杨川那娃厉害,我后来是干不赢他了,我后来也发现他的绝招了。我问什么绝招,木乃说,他喝酒时旁边放几瓶水,喝一口酒就喝一大口水,我是干不赢他呀!
木乃50岁左右,小时候生病,家贫又没及时治,一只脚留下了残疾。他长着一双小眼睛,但精神气十足,说话表情丰富,神采飞扬的。从言语间看得出,木乃是佩服并喜欢杨川的。我随意问了句杨川怎么样,木乃抿着嘴使劲点了点头说,这娃可以哟!对我们很上心。特别是刚种下凤凰李那十多天,天天往山上跑,天天求老天爷下雨,到了地里就趴在那看苗子长,好笑得很哟!我老婆生娃我都没这么尽心。可惜呀,这娃为了我们把女朋友都整吹了,我这心里很不好受呀。说这话时,木乃一边用拳头捶着心口,眼睛都湿了,这不由让我有些惊讶和感动。当然,这是后话。
就这样,在和村民的熟悉中,杨川对扶贫工作的具体内容和任务也逐渐清晰起来,什么建卡户、非建卡户,什么“两不愁三保障”,杨川张口就来,还有些自得。只是,杨川没想到,烦恼很快就来了。
一开始,杨川还是热血沸腾、充满理想的。他搞清楚了村里的贫困情况,心里也有了打算。不是有句话吗,要想富,先修路。他要想办法先把通村路修好,然后帮村民建起发展产业,让贫穷永远不再来;然后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文明生活走进每个村民家中。
的确,这些想法都很好,也很让人兴奋,当然也让他自己激动不已。但这些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眼下正在做的事却遇上了麻烦。
按照上级的要求,为了把党的扶贫政策真正落实好,需要重新对上报的贫困建卡户进行甄别。杨川这时才晓得,村民刚开始对当贫困户其实并不热心,有的还觉得当了没面子,特别是涉及到娶媳嫁女,谁愿意摊上个贫困户的亲家呀!但随着扶贫政策的进一步透明,村民们忽然发现,当上贫困户有很多好处,后来传得更邪乎,只要当上贫困户,国家就把你包到老,吃穿不用愁,坐着就享福。面子有什么用?面子能管你一辈子吗?于是,村民们从不想当变成了争着当,天天都有上村上、上镇上去闹的。都是乡里乡亲的,给谁不给谁,还真不好办。贫困户的指标怎么分到户的,就不好说了。这里面,有的是真贫困,有的是为了息事宁人,有的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就像很多事一样,原本是好好的政策,一落实起来就硬生生变了味。好在政府发现及时,从县到镇都发了话:必须纠偏。
而这一说难不难、说不难又难的事就落在了这些驻村书记们的肩上,杨川自然也在其中。这说来似乎有道理,毕竟驻村书记都是外来人,没有乡里乡亲的这层关系羁绊,可以放开手脚调整。
按政策办,肯定不难。杨川也是这样想的,这贫困建卡户的标准是有的呀,怎么会搞错。但后来,他也理解了村干部的难处,深深感到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易。
“小书记,你是来扶贫的吧?这次能发什么东西?还是要发钱?什么时候钱才能下来?”一进村,村民就围着杨川不住地问。杨川哭笑不得,这根本没法回答嘛。他手里拿着村委会此前给他准备的贫困户名单,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问王支书,这贫困户名单当时到底是如何确定的。
王支书倒也毫不避讳,“抓阄呀!”
“抓阄?”杨川一时还没明白过来。王支书接着说:“是呀,乡里乡亲的,给谁不给谁都不公平,我们用的最公平的法子,抓阄,村民们都很信服,不会有矛盾。”
杨川心里说不出的苦,这怎会没矛盾?
接连几天,杨川走村入户,跟老乡拉家常、摆情况,发现了抓阄确定贫困户名单的弊——一些确实贫困的村民没有享受到党的扶贫政策,将会给下一步的扶贫工作开展造成很大困难,而一些脖子上挂着金项链的人也在要贫困户。到这时,杨川才终于明白中央为什么把这次扶贫定位为精准扶贫的深刻含义。
中央真是高瞻远瞩呀!杨川心里感慨万分,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真正的公平就是要用事实说话,谁家“贫”,谁家“不贫”,要依据指标事实来定。而这一切,就要靠一户一户的摸排掌握。
让扶贫更精准,让需要帮助的人享受到党的好政策,这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入村后的一个月,杨川天天待在村里,几乎把每一家都跑遍了,拿出了新的贫困户名单,按照国家、省扶贫政策所定标准,重新认定、精准识别67户贫困户,公示公开。
原以为这样做就没问题了,原以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真正的贫困户重新争取到了利益,杨川心里被一种成功的快乐包裹着。那些天,每晚都回去得很晚,但他一点不觉得辛苦,每天回去的脚步都是轻快的。每每看到村民脸上回报的笑意,他感到被大家认可、被别人需要是一件幸福的事。杨川还是想得太天真了。他忘了,或者是忽略了,那些被撤掉贫困户的人家心里是多么的不服。
寒冬的一天,杨川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已是晚上9点多了。他匆匆收拾好文件走出村委会,他还有几公里的路要赶。走出房门,外边漆黑一片,偶尔有村舍昏暗的灯光零星地晃过。不料,刚出村口,他就被一户村民强行拦住,不让走,非要让他给个交代,为什么自己会被从贫困户的名单中摘出来,说不清楚就不能离开。
没见过这阵式的杨川一下给吓住了,怯怯地说,你家的情况不够标……
村民可不依了,什么不够标准,都是一亩三分地,都有一双手,我靠自己双手还错啦?人家好吃懒做还要帮,还要补助奖励,你们是什么政策、什么标准?
无论怎样说,就没法说清,说到底,不答应就别想走人。黑灯瞎火的村边,不断聚拢着人,杨川第一次感到了孤立无援的悲哀,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而孤单。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在他记忆里,这是他人生记事来的第一次。尽管他已是带着哭腔在解释,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他突然感到是那样的疲惫,真想能立马倒在床上好好躺躺……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幸亏镇长从村上路过,闻声赶来,把那位村民吼住,杨川才得以抽身离开。
而这件事也让杨川更加明白,政策的落实不是一件小事,要让每一位村民都信服,还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策知识储备。
此后,村支书陪着杨川,上门做政策宣传,摆事实、讲道理。家里有几口人、分别做什么、兄弟在哪里务工、家里的住房情况、有没有小汽车……见自家的情况外来的小书记都清清楚楚,村民知道,这个小书记不简单,名单没有掺水,一户一户都是有依据的,不得不服了。而对于杨川来说,犹如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精准识别贫困户这项任务总算完成,可以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计划了。
杨川说,走访村民的这段日子对自己帮助很大,一方面逼迫自己提升了政策水平,另一方面还加深了与村民的沟通,增进了了解。就这样,他与村民走近了,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个可爱的小书记。
村里有一个叫罗明云的哑巴,生来就不会说话,40多岁了还未娶妻,一直独居。长期的孤独生活让他成天就靠喝酒打发日子,每天都是醉醺醺的,家里也不收拾,床上脏衣被子堆成一团,屋里一股怪味。杨川在走访中,跟他聊天,鼓励他戒酒,给他讲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的道理。看着这个从省城来的又高又帅气的书记一点没架子地和自己拉家常,罗明云内心很感动。他很看重这个小书记,虽然他说不出来,但可以用点头来表示,杨书记劝他的话他要听,后来果真把酒戒了。杨川几次从他家门前过,都被他热情地拉到自己屋子里,不住比划。住在隔壁的兄嫂连忙过来跟杨川解释说,自从杨书记跟罗明云聊过后,他就把自己屋子门前渠里的杂草都清得干干净净的,也不喝酒了,每天把自己打收拾得干干净净。
杨川心里很是感动,自己微薄的力量原来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人。他深深地感到,这些普普通通的山里人其实都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他们缺的是关心,需要有人来引导。随后,杨川积极奔走努力,为罗明云办理了低保和医疗保险,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工作,现在罗明云脸上不再是木讷的表情,不再是阴云布满的表情,脸上多了一分笑容,多了一分想要表达的喜悦,整个人也都清爽了起来。
关键时候,杨川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采访中,老村长告诉我,杨川这个娃很招人喜欢,点子多。杨川说其实不是他点子多,而是很着急。他在走访的过程中,总会情不自禁地思考一个问题,若这样一个一个地帮,何时是头呀!要想让村民们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发展产业,让大家共同致富才行,可发展什么产业呢?这个问题萦绕在心头,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禁不住多听多问多看。
有人说杨川会要政策,主要是长得帅、交际广。有人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桥段,说是县领导下基层,如果不是常委,让电视台派人都很难派得出,但如果让杨川出面请,就怎么也抽得出人来,而且绝对是美女出场。其实,通过与杨川的接触,我认为杨川的形象自然是一个优势,但他也有很多优点,喜欢和别人交流,而且很真诚,无形中人缘就好,了解的信息也就自然多了。
其实,用心,总会有思路;用情,枯树也会开花。一次,在与一起来的驻村扶贫农技人员的闲聊中,杨川嗅到了一丝灵感——种植特色农产品——种凤凰李有前景!
原本人家也只是说一说,随口提了个建议。但杨川却认真了,觉得可以干。他立马上网查资料,了解到凤凰李又名一点红、五月脆,脆甜脱骨、肉质细腻,甜度可以达到18。不仅如此,这种李子还特别耐运输,作为李子中的翘楚,凤凰李生长迅速、见效快,种植3年半就可达到丰产。
想到就去干,而且要做大,要有规模,搞个千亩果园。
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干事得要钱呀,这钱从哪里来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他所在的单位领导作了汇报,学院领导十分支持,让他大胆去干,并答应拔付10万元作启动资金。
这下杨川热情高涨了——他忽然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呀,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呀!有学院,还有省地矿局,杨川信心百倍,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接下来的日子,听说眉山搞得好,他便带队跑去考察,从种植品种到种植技术,从种植时间到成本核算,都问得清清楚楚,本子记了一大本。随后,他又联系农技部门测定土壤成分。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杨川跟村委会一起研究,正式决定在兰池村发展凤凰李产业,其开展形式也结合村情实际,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坚持“长短、种养、林上林下、农旅”四结合的规划布局原则,探索出一条符合兰池村村情的扶贫工作新路子。
杨川告诉我,这个凤凰李“四结合”的含义就是,一是凤凰李3年要见成效且长远受益,同时结合林下经济种植南瓜短期增收;二是将种植凤凰李、果桑等与养殖业(养猪、羊)相结合;三是林上种植凤凰李,林下即在凤凰李树下的间隙种植南瓜,合理有效整合土地资源;四是发展农业为乡村旅游打下坚实基础,发展农村经济带动乡村振兴。
随后,他又将方案送到镇上、县上,不仅得到镇上的支持,也得到了县上的肯定,表示可以作为今后全县的一个试点或者示范项目。这少不得就有实质性的支持力度呀,这不等于中奖了吗?杨川心中暗喜。
目标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实施。为了尽早推行,杨川组织人员赶到眉山,连夜押车将15600棵凤凰李幼苗拉回了村里。
人一兴奋起来就不觉得累,杨川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那天下午4点出发,与村支书换班开车,驱车7小时,凌晨12点赶到眉山,树苗装车后已是后半夜1点。为了保证树苗成活率,又马不停蹄往回赶,连夜从眉山拉回树苗,早晨赶回村子后,就发动村民第一时间将树苗移栽到土壤里。
树苗栽下去后那些日子,村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小书记天天往地里跑,天天蹲在那,甚至有时是趴在那,巴巴地盼着树苗快发芽。住附近的木乃说,老婆生娃儿我都没那个样,杨川这娃真的可以哟。
其间,为了说服村民把荒地拿来种凤凰李,杨川也是颇费了些口舌。按理,村民的地荒着也是荒着,交给公司,一亩地第一年可流转200元,每年递增;收入再分红,另外参加公司管理还有每天80元的务工费,按说这于村民来说是多好的事,但偏偏有村民不愿意,也不那样想。原来,他们平时地里种的是玉米,虽说收入不高,但他们认为自己心里有数,至少不会有闪失。拿去种什么凤凰李,谁知道会不会一场空,心里还真是不踏实。就是宁愿空着什么不种都好。
为此,杨川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讲形势、讲党的政策、讲科学技术、讲政策兜底,然后又发动其他村民做工作,好在总算都通了。
“以前总想着自己有点残疾吧,家庭条件又差,就希望等着国家来扶持。”这当中,木乃不日算是兰池村贫困户中的一个代表,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从前基本靠传统种植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现在小杨书记带着我们搞凤凰李,我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产业,致富有望了。”这年,木乃全家亲自参与新兴产业凤凰李种植,土地全部入股分红。
2017年,在兰池村一组的山坡上,一大片地种上了凤凰李。这260亩凤凰李虽然还没长大,但已经可以看到它未来迷人的景象了,来年还要再扩大,达到千亩果园规模,并让这一带成为美丽的景点,这是杨川和村委们的梦想。这让所有的人一想起来都是很激动的,只要想一想,那幸福的影子便在眼前飘荡,压根儿就没想到后来还会有几多坎坷。当然,这是后话了……
2019年4月,杨川十分不舍地告别了兰池村这块浸透着他汗水和梦想的热土,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原本规定下来扶贫2年,却没想到一干就是4年多。杨川说,离开村子的那天,一位老大娘握着他的手,反复地说,“小杨书记,你不走嘛,你不走嘛……不走行不行……”杨川说:“当时,我真的有一种冲动,想放下行李,给队上写个申请,再继续留下来干到底!”
我相信杨川说的是真心话,因为4年多的时间在人生中虽只是一瞬,但这段经历却是十分宝贵难忘的,尤其是刚刚开创的扶贫产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还有很多村民等着他去帮,但组织上认为他应该回来了。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徐振川说:“一方面这是学院从培养更多干部的原因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从关心扶贫干部个人生活考虑。”院长林仕发告诉我,从杨川这几年的成长看得出,把年轻干部放到扶贫一线去是对的,的确很锻炼人,所以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锻炼。
尽管言语间有些回避和闪躲,我还是感觉出杨川的个人问题受到了一些影响。在采访中,村民和他的同事告诉我,杨川把心思放在了村民的帮扶上,有段时间和女朋友的关系似乎很紧张,晚上电话一打就很久,打过后情绪就很差,2016年底,女朋友就吹了。我向杨川打听这事的时候,他一直不肯谈,并央求说能不能不提这事。看得出,杨川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我只能想象,原本两个热恋的年轻人突然天各一方,两人都有各自的事业,一开始还记得通通电话互相问候,可随着工作任务和压力的加重、作息时间的不同,联系也渐渐少了,自然矛盾也就产生了……
但对于来甘洛扶贫,杨川一点儿不后悔,否则也不会有还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毕竟,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2018年,省上加强了扶贫力度,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局里又增派了36名干部分别前往各个村,杨川身边一下来了4名战友,力量和信心倍增,在大家齐心戮力下,兰池村悄然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路变了。杨川通过努力奔走寻求政策和经费支持,在村内铺就了约4.7公里的通村硬化公路,并实现了公路到户,泥泞的羊肠小道变为宽阔平整的大路。
产业有了。杨川和村两委在省地矿局及帮扶单位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和108地质队的支持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抓住脱贫攻坚机遇,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按照“长短、种养、林上林下、农旅”四结合的规划布局原则,发展了台湾密本南瓜和凤凰李种植项目,实现脱贫项目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精准定位,着力打造出兰池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雏形。2017年凤凰李种植260亩,2018年种植740亩,并引进果桑种植520亩,集中建成村集体经济产业园区1000亩,预计可带来种植收益900万元左右,实现全村1065人,年人均产业收入预计在0.8万元左右。